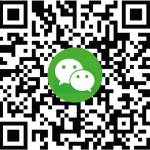留一扇半掩的门,是拒绝在一个探问尚未低语出所有答案之前,就将其关闭。
因为静止并非运动的缺席,而是运动最微妙的动态。
注:此处我使用「探问」而非「问题」,是为了强调其过程性,如同觉察所描述的内在运动。
变化并非始于行动,而是始于觉察。觉察——这一唤醒自我、唤醒自身模式与局限的主动过程——是所有转化的第一步。
这一过程常被总结为如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:「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。」它已成为心理学和个人发展领域的基石。
然而,这句话常常隐含地暗示:改变是目的本身——这限制了我们的选择。
如同费登奎斯(身体教育的先驱)所言:「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所觉知的。」
在改变一个动作、一个习惯或一个信念之前,我们必须先觉知它,如同在黑暗的房间里点亮一盏灯。这一阶段并非被动:它需要细腻的注意力、无评判的好奇心,以及常常需要勇气去看清之前未曾察觉的事物。
因此,觉察不是一种状态,而是一个过程,一种内在的运动。

但觉察并未止步于此。一旦光明被点亮,一个问题浮现:如何运用这份清明?
当觉知被唤醒,**问题变为:「改变是必要的吗?」**或「我必须改变吗?」
别的过程并非冷冰冰的分析,而是一场内在对话,我们的情绪和价值体系在此成为指南针。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:在一场紧张的讨论中,选择不以尖锐的回击回应——即使它看似合理——可能是一种尊重的行为。尊重他人(价值体系的一部分),也尊重我们自身的完整性(对恐惧情绪的回应)。这种对即时反应的有意放下,并非软弱,而是对「什么比短暂的胜利更重要」的肯定:保持一段尊重的关系,或仅仅是内心的平静。
因此,选择不改变,选择静止——不屈服于冲动、社会期待或旧习新习——可以是一种一致性的行为。这不是放弃,而是一种主动的决定,忠于此时此刻定义我们的核心。
辨别这一步骤常被忽视,尽管它至关重要。在一个崇尚行动和生产力的社会中,停下来评估可能显得反直觉。然而,如同克里希那穆提所提醒的:「努力即是抗拒。」强行推动与自身深层需求不符的改变,可能制造的紧张多于解决方案。
辨别需要倾听——倾听身体、情绪和环境——以区分外在强制与内在必要。有时,答案是不改变。而这正是此选择的力量所在。
在一个痴迷于永恒转化的文化中,选择不改变可能显得矛盾。然而,这一选择本身即是一种改变:它打破了「改变总是等同于积极转化」的幻象。
例如,动中觉察教导我们,真正的流动性常源于有意识的停顿——那些我们停止挣扎、更好地感知「已然存在之物」的时刻。表面的静止于是成为一种勇气:不是屈服,而是一个可能性显现的空间。它揭示了我们所谓的「稳定」,往往只是一种幻象——一种在无形力量之间的脆弱平衡。如同量子物理学中,观察本身改变了被观察者——选择不作为本身也是一种作为。

我想到一次 身心咨询 个案,与一位名为「桑德拉」的参与者在我的工作坊中共事。桑德拉能够言语上轻易表达对母亲的愤怒,但在身体上却无法表达。在我们的交流中,她的愤怒转化为一种身体化的恐惧,而她无法用语言表达。显然,她不允许自己向母亲表达恐惧,也不允许自己表现出攻击性。对于桑德拉,新的门扉打开了,而这些门可以保持半掩状态,只要辨别的过程仍然活跃。
表面看来,选择不改变从不是终点。它是一道门槛。通过拒绝在紧迫感、习惯或「必须改变」的命令下行动,我们创造出一个空的空间——一个开放的空间,让选择可以被重新审视、重新想象。
这种表面的静止并非一堵墙,而是一扇半掩的门:它让我们得以在日后以全新的视角回到问题。有意识的「不选择」于是成为无意识决策流中的一口气息。它消解了「静止不变」的幻象,揭示出所有的「固定」都只是暂时的选择——而自由正在于我们重新审视确定性的能力。
身体深知这一点:即使看似静止,我们的细胞不断更新,肌肉微调张力,神经系统持续重新校准。仅仅是呼吸,便是一场看不见的运动,穿越并转化我们的身体,改变我们的平衡——无论站立或坐姿——而我们往往毫无觉知。
觉察终将向我们揭示: 改变不是一种被动的选项,而是当下生命的体验。
因此,问题不再是「我是否必须改变?」,而是: 「我如何选择——或不选择——参与这一流动?」
说到底,问题与其说是「我们是谁?」,不如说是: 「我们如何对待塑造我们的一切?」 ——而正是在这份有意识的参与中,在「是」与「否」之间,我们的真正力量得以显现。
引用:「真正的自由,是能够对自己说‘不’。」
(灵感来自阿尔贝·加缪)

不要忘记查看我们即将举行的活动和课程的日历。
Don’t forget to check the calendar of our upcoming events and classes.